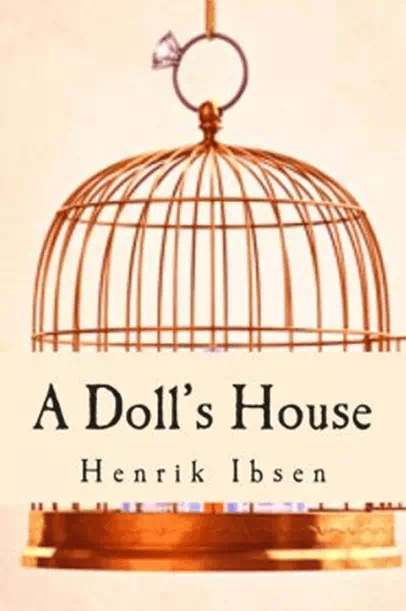选自《易卜生文集》第五卷(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)。潘家洵译。
易卜生(1828—1906),挪威剧作家。
《玩偶之家》的主要情节是:娜拉与丈夫海尔茂结婚八年,一直相信丈夫深爱着自己。多年前,娜拉为给海尔茂治病,伪造父亲的签名向海尔茂的同事、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借过一笔款子。柯洛克斯泰为保住自己的职位,以这件事威胁娜拉。海尔茂得知此事后,先是勃然大怒,在柯洛克斯泰归还当年的借据后又态度大变,以为娜拉会接受自己的“饶恕”。娜拉看穿了海尔茂的本质,领悟到自己在婚姻中只是丈夫的玩偶,毅然离家出走。
《玩偶之家》演出图
第三幕
…………
海尔茂 ( 送她到门口)明天见,明天见,一路平安。我本来该送你回去,可是好在路很近。再见,再见。(林丹太太走出去,海尔茂关上大门回到屋子里)好了,好容易才把她打发走。这个女人真啰唆!
娜 拉 你累了吧,托伐?
海尔茂 一点儿都不累。
娜 拉 也不想睡觉?
海尔茂 一点儿都不想。精神觉得特别好。你呢?你好像又累又想睡。
娜 拉 是,我很累。我就要去睡觉。
海尔茂 你看!我不让你再跳舞不算错吧?
娜 拉 喔,你做的事都不错。
海尔茂 ( 亲她的前额)我的小鸟儿这回说话懂道理。你看见没有,今儿晚上阮克真高兴!
娜 拉 是吗?他居然很高兴?我没跟他说过话。
海尔茂 我也只跟他说了一两句。可是我好久没看见他兴致这么好了。(对她看了会儿,把身子凑过去)回到自己家里,静悄悄的只有咱们两个人,滋味多么好!喔,迷人的小东西!
娜 拉 别那么瞧我。
海尔茂 难道我不该瞧我的好宝贝儿——我一个人的亲宝贝儿?
娜 拉 (走到桌子那边)今天晚上你别跟我说这些话。
海尔茂 ( 跟过来)你血管里还在跳塔兰特拉[1]——所以你今天晚上格外惹人爱。你听,楼上的客要走了。(声音放低些)娜拉,再过一会儿整个这所房子里就静悄悄的没有声音了。
娜 拉 我想是吧。
海尔茂 是啊,我的娜拉。咱们出去做客的时候我不大跟你说话,我故意避开你,偶然偷看你一眼,你知道为什么?因为我心里好像觉得咱们偷偷地在恋爱,偷偷地订了婚,谁也不知道咱们的关系。
娜 拉 是,是,是,我知道你的心都在我身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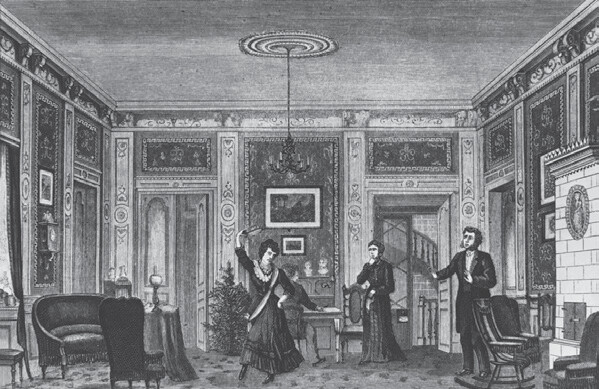
《玩偶之家》演出图
海尔茂 到了要回家的时候,我把披肩搭上你的滑溜的肩膀,围着你的娇嫩的脖子,我心里好像觉得你是我的新娘子,咱们刚结婚,我头一次把你带回家——头一次跟你待在一块儿,头一次陪着你这娇滴滴的小宝贝儿!今天晚上我什么都没想,只是想你一个人。刚才跳舞的时候,我看见你那些轻巧活泼的身段,我的心也跳得按捺不住了,所以那么早我就把你拉下楼。
娜 拉 走开,托伐!撒手,我不爱听这些话。
海尔茂 什么?你成心逗我吗,娜拉?你不爱听!难道我不是你丈夫?(有人敲大门)
娜 拉 (吃惊)你听见没有?
海尔茂 ( 走到门厅里)谁?
阮 克 ( 在外面)是我。我能不能进来坐会儿?
海尔茂 ( 低声叽咕)讨厌!这时候他还来干什么?(高声)等一等!(开门)请进,谢谢你从来不肯过门不入。
阮 克 我走过这儿好像听见你说话的声音,因此就忍不住想进来坐一坐。(四面望望)啊,这个亲热的老地方!你们俩在这儿真快活,真舒服!
海尔茂 刚才你在楼上好像也觉得很受用。
阮 克 很受用,为什么不受用?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能享受为什么不享受?能享受多少就算多少,能享受多久就算多久。今晚的酒可真好。
海尔茂 香槟酒特别好。
阮 克 你也觉得好?我喝了那么多,说起来别人也不信。
娜 拉 托伐喝的香槟酒也不少。
阮 克 是吗?
娜 拉 真的,他喝了酒兴致总是这么好。
阮 克 辛苦了一天,晚上喝点儿酒没什么不应该。
海尔茂 辛苦了一天!这句话我可不配说。
阮 克 ( 在海尔茂肩膀上拍一下)我倒可以说这句话。
娜 拉 阮克大夫,你是不是刚做完科学研究?
阮 克 一点儿都不错。
海尔茂 你听!小娜拉也谈起科学研究来了!
娜 拉 结果怎么样,是不是可以给你道喜?
阮 克 可以。
娜 拉 这么说,结果很好?
阮 克 好极了,对大夫也好,对病人也好,结果是确实无疑的。
娜 拉 (追问)确实无疑?
阮 克 绝对地确实无疑。知道了这样的结果,你说难道我还不应该痛快一晚上?
娜 拉 不错,很应该,阮克大夫。
海尔茂 我也这么说,只要你明天不还账。
阮 克 在这世界上没有白拿的东西,什么全都得还账。
娜 拉 阮克大夫,我知道你很喜欢化装跳舞会。
阮 克 是,只要有新奇打扮,我就喜欢。
娜 拉 我问你,下次化装跳舞会咱们俩应该打扮成什么?
海尔茂 不懂事的孩子!已经想到下次跳舞会了!
阮 克 你问咱们俩打扮成什么?我告诉你,你打扮成个仙女。
海尔茂 好,可是仙女该怎么打扮?
阮 克 仙女不用打扮,只穿家常衣服就行。
海尔茂 你真会说!你自己打扮成什么角色呢?
阮 克 喔,我的好朋友,我早打定主意了。
海尔茂 什么主意?
阮 克 下次开化装跳舞会的时候,我要扮隐身人。
海尔茂 这话真逗人。
阮 克 我要戴一顶大黑帽子——你们没听说过眼睛瞧不见的帽子吗?帽子一套在头上,人家就看不见你了。
海尔茂 ( 忍住笑)是,是。
阮 克 哦,我忘了进来干什么了。海尔茂,给我一支雪茄烟——要那种黑的哈瓦那。
海尔茂 请。(把雪茄烟盒递过去)
阮 克 ( 拿了一支烟,把烟头切掉)谢谢。
娜 拉 ( 给他划火柴)我给你点烟。
阮 克 谢谢,谢谢!(娜拉拿着火柴,阮克就着火点烟)现在我要跟你们告别了!
海尔茂 再见,再见!老朋友!
娜 拉 阮克大夫,祝你安眠。
阮 克 谢谢你。
娜 拉 你也应该照样祝我。
阮 克 祝你?好吧,既然你要我说,我就说。祝你安眠,谢谢你给我点烟。
阮克向他们点点头,走出去
海尔茂 ( 低声)他喝得太多了。
娜 拉 ( 心不在焉)大概是吧。(海尔茂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来,走进门厅)托伐,你出去干什么?
海尔茂 我把信箱倒一倒,里头东西都满了,明天早上报纸装不下了。
娜 拉 今晚你工作不工作?
海尔茂 你不是知道我今晚不工作吗?唔,这是怎么回事?有人弄过锁。
娜 拉 弄过锁?
海尔茂 一定是。这是怎么回事?我想用人不会——?这儿有只撅折的头发夹子。娜拉,这是你常用的。
娜 拉 ( 急忙接嘴)一定是孩子们——
海尔茂 你得管教他们别这么胡闹。好!好容易开开了。(把信箱里的信件拿出来,朝着厨房喊道)爱伦,爱伦,把门厅的灯吹灭了。(拿着信件回到屋里,关上门)你瞧,攒了这么一大堆。(把整叠信件翻过来)哦,这是什么?
娜 拉 ( 在窗口)那封信!喔,托伐,别看!
海尔茂 有两张名片,是阮克大夫的。
娜 拉 阮克大夫的?
海尔茂 ( 瞧名片)阮克大夫。这两张名片在上头,一定是他刚扔进去的。
娜 拉 名片上写着什么没有?
海尔茂 他的名字上头有个黑十字。你瞧,多么不吉利!好像他给自己报死信。
娜 拉 他是这意思。
海尔茂 什么!你知道这件事?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?
娜 拉 他说了。他说给咱们这两张名片的意思就是跟咱们告别。他以后就在家里关着门等死。
海尔茂 真可怜!我早知道他活不长,可是没想到这么快!像一只受伤的野兽爬到窝里藏起来!
娜 拉 一个人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最好还是静悄悄地死。托伐,你说对不对?
海尔茂 ( 走来走去)这些年他跟咱们的生活已经结合成一片,我不能想象他会离开咱们。他的痛苦和寂寞比起咱们的幸福好像乌云衬托着太阳,苦乐格外分明。这样也许倒好——至少对他很好。(站住)娜拉,对于咱们也未必不好。现在只剩下咱们俩,靠得更紧了。(搂着她)亲爱的宝贝儿!我总是觉得把你搂得不够紧。娜拉,你知道不知道,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,好让我拼着命,牺牲一切去救你。
娜 拉 ( 从他怀里挣出来,斩钉截铁的口气)托伐,现在你可以看信了。
海尔茂 不,不,今晚我不看信。今晚我要陪着你,我的好宝贝儿。
娜 拉 想着快死的朋友,你还有心肠陪我?
海尔茂 你说的不错。想起这件事咱们心里都很难受。丑恶的事情把咱们分开了,想起死人真扫兴。咱们得想法子撇开这些念头。咱们暂且各自回到屋里去吧。
娜 拉 ( 搂着他脖子)托伐!明天见!明天见!
海尔茂 ( 亲她的前额)明天见,我的小鸟儿。好好儿睡觉,娜拉!我去看信了。
他拿了那些信走进自己的书房,随手关上门。
娜 拉 ( 瞪着眼瞎摸,抓起海尔茂的舞衣披在自己身上,急急忙忙,断断续续,哑着嗓子,低声自言自语)从今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!永远见不着了,永远见不着了。(把披肩蒙在头上)也见不着孩子们了!永远见不着了!喔,漆黑冰凉的水!没底的海!快点儿完事多好啊!现在他已经拿着信了,正在看!喔,还没看。再见,托伐!再见,孩子们!
她正朝着门厅跑出去,海尔茂猛然推开门,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,站在门口。
海尔茂 娜拉!
娜 拉 ( 叫起来)啊!
海尔茂 这是谁的信?你知道信里说的什么事?
娜 拉 我知道。快让我走!让我出去娜拉想出去投水自杀 !
海尔茂 ( 拉住她)你上哪儿去?
娜 拉 ( 竭力想脱身)别拉着我,托伐。
海尔茂 ( 惊慌倒退)真有这件事?他信里的话难道是真的?不会,不会,不会是真的。
娜 拉 全是真的。我只知道爱你,别的什么都不管。
海尔茂 哼,别这么花言巧语的!
娜 拉 ( 走近他一步)托伐!
海尔茂 你这坏东西——干的好事情!
娜 拉 让我走——你别拦着我!我做的坏事不用你担当!
海尔茂 不用装腔作势给我看。(把出去的门锁上)我要你老老实实把事情招出来,不许走。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事?快说!你知道吗?
娜 拉 ( 眼睛盯着他,态度越来越冷静)嗯,现在我才完全明白了。
海尔茂 ( 走来走去)嘿!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!这八年工夫——我最得意、 最喜欢的女人——没想到是个伪君子,是个撒谎的人——比这还坏——是个犯罪的人。真是可恶极了!哼!哼!(娜拉不作声,只用眼睛盯着他)其实我早就该知道。我早该料到这一步。你父亲的坏德行——
(娜拉正要说话)少说话!你父亲的坏德行,你全都沾上了——不信宗教,不讲道德,没有责任心。当初我给他遮盖,如今遭了这么个报应!我帮你父亲都是为了你,没想到现在你这么报答我!
娜 拉 不错,这么报答你。
海尔茂 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。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。喔,想起来真可怕!现在我让一个坏蛋抓在手心里。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,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。他可以随便摆布我,我不能不依他。我这场大祸都是一个下贱女人惹出来的!
娜 拉 我死了你就没事了。
海尔茂 哼,少说骗人的话。你父亲从前也老有那么一大套。照你说,就是你死了,我有什么好处?一点儿好处都没有。他还是可以把事情宣布出去,人家甚至还会疑惑我是跟你串通一气的,疑惑是我出主意撺掇你干的。这些事情我都得谢谢你——结婚以来我疼了你这些年,想不到你这么报答我。现在你明白你给我惹的是什么祸吗?
娜 拉 ( 冷静安详)我明白。
海尔茂 这件事真是想不到,我简直摸不着头脑。可是咱们好歹得商量个办法。把披肩摘下来。摘下来,听见没有!我先得想个办法稳住他,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知道。咱们俩,表面上照样过日子——不要改变样子,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话?当然你还得在这儿住下去。可是孩子不能再交在你手里。我不敢再把他们交给你——唉,我对你说这么一句话心里真难受,因为你一向是我最心爱并且现在还——!可是现在情形已经改变了。从今以后再说不上什么幸福不幸福,只有想法子怎么挽救、怎么遮盖、怎么维持这个残破的局面——(门铃响起来,海尔茂吓了一跳)什么事?三更半夜的!难道事情发作了?难道他——娜拉,你快藏起来,只推托有病。(娜拉站着不动。海尔茂走过去开门)
爱 伦 (披着衣服在门厅里)太太,您有封信。
海尔茂 给我。(把信抢过来,关上门)果然是他的。你别看。我念给你听。
娜 拉 快念!
海尔茂 ( 凑着灯光)我几乎不敢看这封信。说不定咱们俩都会完蛋。也罢,反正总得看。(慌忙拆信,看了几行之后发现信里夹着一张纸,马上快活得叫起来)娜拉!(娜拉莫名其妙地瞧着他)
海尔茂 娜拉!喔,别忙!让我再看一遍!不错,不错!我没事了!娜拉,我没事了!
娜 拉 我呢?
海尔茂 当然你也没事了,咱们俩都没事了。你看,他把借据还你了。他在信里说,这件事非常抱歉,要请你原谅,他又说他现在交了运——喔,管他还写些什么。娜拉,咱们没事了!现在没人能害你了。喔,娜拉,娜拉——咱们先把这害人的东西消灭了再说。让我再看看——(朝着借据瞟了一眼)喔,我不想再看它,只当是做了一场梦。(把借据和柯洛克斯泰的两封信一齐都撕掉,扔在火炉里,看它们烧)好!烧掉了!他说自从24号起——喔,娜拉,这三天你一定很难过。
娜 拉 这三天我真不好过。
海尔茂 你心里难过,想不出好办法,只能——喔,现在别再想那可怕的事情了。我们只应该高高兴兴地多说几遍:“现在没事了,现在没事了!”听见没有,娜拉!你好像不明白。我告诉你,现在没事了。你为什么绷着脸不说话?喔,我的可怜的娜拉,我明白了,你以为我还没饶恕你。娜拉,我赌咒,我已经饶恕你了。我知道你干那件事都是因为爱我。
娜 拉 这倒是实话。
海尔茂 你正像做老婆的应该爱丈夫那样地爱我。只是你没有经验,用错了方法。可是难道因为你自己没主意,我就不爱你吗?我决不会。你只要一心一意依赖我,我会指点你,教导你。正因为你自己没办法,所以我格外爱你,要不然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?刚才我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,心里一害怕,就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,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娜拉,我已经饶恕你了。我赌咒不再埋怨你。
娜 拉 谢谢你饶恕我。(从右边走出去)
海尔茂 别走!(向门洞里张望)你要干什么?
娜 拉 ( 在里屋)我去脱掉跳舞的服装。
海尔茂 ( 在门洞里)好,去吧。受惊的小鸟儿,别害怕,定定神,把心静下来。你放心,一切事情都有我。我的翅膀宽,可以保护你。(在门口走来走去)喔,娜拉,咱们的家多可爱,多舒服!你在这儿很安全,我可以保护你,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来的小鸽子一样。我不久就能让你那颗扑扑跳的心定下来,娜拉,你放心。到了明天,事情就不一样了,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。我不用再说我已经饶恕你,你心里自然会明白我不是说假话。难道我舍得把你撵出去?别说撵出去,就说是责备,难道我舍得责备你?娜拉,你不懂得男子汉的好心肠。要是男人饶恕了他老婆——真正饶恕了她,从心坎里饶恕了她——他心里会有一股没法子形容的好滋味。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。做老婆的就像重新投了胎,不但是她丈夫的老婆,并且还是她丈夫的孩子。从今以后,你就是我的孩子,我的吓坏了的可怜的小宝贝儿。别着急,娜拉,只要你老老实实对待我,你的事情都由我做主,都由我指点。(娜拉换了家常衣服走进来)怎么,你还不睡觉?又换衣服干什么?
娜 拉 不错,我把衣服换掉了。
海尔茂 这么晚还换衣服干什么?
娜 拉 今晚我不睡觉。
海尔茂 可是,娜拉——
娜 拉 ( 看自己的表)时候还不算晚。托伐,坐下,咱们有好些话要谈一谈。(她在桌子一头坐下)
海尔茂 娜拉,这是什么意思?你的脸色铁板冰冷的——
娜 拉 坐下。一下子说不完。我有好些话跟你谈。
海尔茂 ( 在桌子那一头坐下)娜拉,你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不了解你。
娜 拉 这话说得对,你不了解我,我也到今天晚上才了解你。别打岔。听我说下去。托伐,咱们必须把总账算一算。
海尔茂 这话怎么讲?
娜 拉 ( 顿了一顿)现在咱们面对面坐着,你心里有什么感想?
海尔茂 我有什么感想?
娜 拉 咱们结婚已经八年了。你觉得不觉得,这是头一次咱们夫妻正正经经谈谈话?
海尔茂 正正经经!这四个字怎么讲?
娜 拉 这整整的八年——要是从咱们认识的时候算起,其实还不止八年——咱们从来没在正经事情上头谈过一句正经话。
海尔茂 难道要我经常把你不能帮我解决的事情麻烦你?
娜 拉 我不是指着你的业务说。我说的是,咱们从来没坐下来正正经经细谈过一件事。
海尔茂 我的好娜拉,正经事跟你有什么相干?
娜 拉 咱们的问题就在这儿!你从来就没了解过我。我受尽了委屈,先在我父亲手里,后来又在你手里。
海尔茂 这是什么话!你父亲和我这么爱你,你还说受了我们的委屈!
娜 拉 ( 摇头)你们何尝真爱过我,你们爱我只是拿我消遣。
海尔茂 娜拉,这是什么话!
娜 拉 托伐,这是老实话。我在家跟父亲过日子的时候,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,我就跟着他的意见走。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,我也不让他知道,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。他叫我“泥娃娃孩子”,把我当作一件玩意儿,就像我小时候玩我的泥娃娃一样。后来我到你家来住着——
海尔茂 用这种字眼形容咱们的夫妻生活简直不像话!
娜 拉 ( 满不在乎)我是说,我从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你手里。跟你在一块儿,事情都归你安排。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,或者假装爱什么——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——也许有时候真,有时候假。现在我回头想一想,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要饭的叫花子,要一口,吃一口。托伐,我靠着给你耍把戏过日子。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。你和我父亲把我害苦了。我现在这么没出息都要怪你们。
海尔茂 娜拉,你真不讲理,真不知好歹!你在这儿过的日子难道不快活?
娜 拉 不快活。过去我以为快活,其实不快活。
海尔茂 什么!不快活!
娜 拉 说不上快活,不过说说笑笑凑个热闹罢了。你一向待我很好。可是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,从来不谈正经事。在这儿我是你的“玩偶老婆”,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“玩偶女儿”一样。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。你逗着我玩儿,我觉得有意思,正像我逗孩子们,孩子们也觉得有意思。托伐,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。
海尔茂 你这段话虽然说得太过火,倒也有点儿道理。可是以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。玩耍的时候过去了,现在是受教育的时候了。
娜 拉 谁的教育?我的教育还是孩子们的教育?
海尔茂 两方面的,我的好娜拉。
娜 拉 托伐,你不配教育我怎样做个好老婆。
海尔茂 你怎么说这句话?
娜 拉 我配教育我的孩子吗?
海尔茂 娜拉!
娜 拉 刚才你不是说不敢再把孩子交给我吗?
海尔茂 那是气头上的话,你老提它干什么?
娜 拉 其实你的话没说错。我不配教育孩子。要想教育孩子,先得教育我自己。你没资格帮我的忙。我一定得自己干。所以现在我要离开你。
海尔茂 ( 跳起来)你说什么?
娜 拉 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,我得一个人过日子,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。
海尔茂 娜拉!娜拉!
娜 拉 我马上就走。克里斯蒂纳一定会留我过夜。
海尔茂 你疯了!我不让你走!你不许走!
娜 拉 你不许我走也没用。我只带自己的东西。你的东西我一件都不要,现在不要,以后也不要。
海尔茂 你怎么疯到这步田地!
娜 拉 明天我要回家去——回到从前的老家去。在那儿找点儿事情做也许不太难。
海尔茂 喔,像你这么没经验——
娜 拉 我会努力去吸取。
海尔茂 丢了你的家,丢了你丈夫,丢了你儿女!不怕人家说什么话!
娜 拉 人家说什么不在我心上。我只知道我应该这么做。
海尔茂 这话真荒唐!你就这么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?
娜 拉 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?
海尔茂 那还用我说?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。
娜 拉 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。
海尔茂 没有的事!你说的是什么责任?
娜 拉 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。
海尔茂 别的不用说,首先你是一个老婆,一个母亲。娜 拉 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。现在我只信,首先我是一个人,跟你一样的一个人——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。托伐,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,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的。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,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。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,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。
海尔茂 难道你不明白你在自己家庭的地位?难道在这些问题上没有颠扑不破的道理指导你?难道你不信仰宗教?
娜 拉 托伐,不瞒你说,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。
海尔茂 你这话怎么讲?
娜 拉 除了行坚信礼的时候牧师对我说的那套话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牧师告诉过我,宗教是这个,宗教是那个。等我离开这儿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,我也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。我要仔细想一想,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,对我合用不合用。
海尔茂 喔,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话!并且还是从这么个年轻女人嘴里说出来的!要是宗教不能带你走正路,让我唤醒你的良心来帮助你——你大概还有点儿道德观念吧?要是没有,你就干脆说没有。
娜 拉 托伐,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。我实在不明白。这些事情我摸不清。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我也听说,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,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。父亲病得快死了,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。丈夫病得快死了,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!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。
海尔茂 你说这些话像个小孩子。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。
娜 拉 我真不了解。现在我要去学习。我一定要弄清楚,究竟是社会正确,还是我正确。
海尔茂 娜拉,你病了,你在发烧说胡话。我看你像精神错乱了。
娜 拉 我的脑子从来没像今天晚上这么清醒、这么有把握。
海尔茂 你这么清醒、这么有把握,居然要丢掉丈夫和儿女?
娜 拉 一点儿不错。
海尔茂 这么说,只有一句话讲得通。
娜 拉 什么话?
海尔茂 那就是你不爱我了。
娜 拉 不错,我不爱你了。
海尔茂 娜拉!你忍心说这话!
娜 拉 托伐,我说这话心里也难受,因为你一向待我很不错。可是我不能不说这句话。现在我不爱你了。
海尔茂 ( 勉强管住自己)这也是你清醒的有把握的话?
娜 拉 一点儿不错。所以我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。
海尔茂 你能不能说明白,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你不爱我?
娜 拉 能。就因为今天晚上奇迹没出现,我才知道你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种人。
海尔茂 这话我不懂,你再说清楚点儿。
娜 拉 我耐着性子整整等了八年,我当然知道奇迹不会天天有。后来大祸临头的时候,我曾经满怀信心地跟自己说:“奇迹来了!”柯洛克斯泰把信扔在信箱里以后,我绝没想到你会接受他的条件。我满心以为你一定会对他说“尽管宣布吧”,而且你说了这句话之后,还一定会——
海尔茂 一定会怎么样?叫我自己的老婆出丑丢脸,让人家笑骂?
娜 拉 我满心以为你说了那句话之后,还一定会挺身出来,把全部责任担在自己肩膀上,对大家说:“事情都是我干的。”
海尔茂 娜拉——
娜 拉 你以为我会让你替我担当罪名吗?不,当然不会。可是我的话怎么比得上你的话那么容易叫人家相信?这正是我盼望它发生又怕它发生的奇迹。为了不让奇迹发生,我已经准备自杀。
海尔茂 娜拉,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,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。可是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。
娜 拉 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。
海尔茂 喔,你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像个傻孩子。
娜 拉 也许是吧。可是你想的和说的也不像我可以跟他过日子的男人。后来危险过去了——你不是怕我有危险,是怕你自己有危险——不用害怕了,你又装作没事人儿了。你又叫我跟从前一样乖乖地做你的小鸟儿,做你的泥娃娃,说什么以后要格外小心保护我,因为我那么脆弱不中用。(站起来)托伐,就在那当口,我好像忽然从梦里醒过来,我简直跟一个陌生人同居了八年,给他生了三个孩子。喔,想起来真难受!我恨透了自己没出息!
海尔茂 ( 伤心)我明白了,我明白了,在咱们中间出现了一道深沟。可是,娜拉,难道咱们不能把它填平吗?
娜 拉 照我现在这样子,我不能跟你做夫妻。
海尔茂 我有勇气重新再做人。
娜 拉 在你的泥娃娃离开你之后——也许有。
海尔茂 要我跟你分手!不,娜拉,不行!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。
娜 拉 ( 走进右边屋子)要是你不能设想,咱们更应该分开。(拿着外套、帽子和旅行小提包又走出来,把东西搁在桌子旁边椅子上)
海尔茂 娜拉,娜拉,现在别走,明天再走。
娜 拉 ( 穿外套)我不能在陌生人家里过夜。
海尔茂 难道咱们不能像哥哥妹妹那么过日子?
娜 拉 ( 戴帽子)你知道那种日子长不了。(围披肩)托伐,再见。我不去看孩子了。我知道现在照管他们的人比我强得多。照我现在这样子,我对他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。
海尔茂 可是,娜拉,将来总有一天——
娜 拉 那就难说了。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。
海尔茂 无论怎么样,你还是我的老婆。
娜 拉 托伐,我告诉你。我听人说,要是一个女人像我这样从她丈夫家里走出去,按法律说,她就解除了丈夫对她的一切义务。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,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。你不受我拘束,我也不受你拘束。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。拿去,这是你的戒指。把我的也还我。
海尔茂 连戒指都要还?
娜 拉 要还。
海尔茂 拿去。
娜 拉 好。现在事情完了。我把钥匙都搁在这儿。家里的事,用人都知道——她们比我更熟悉。明天我动身之后,克里斯蒂纳会来给我收拾我从家里带来的东西。我会叫她把东西寄给我。
海尔茂 完了!完了!娜拉,你永远不会再想我了吧?
娜 拉 喔,我会时常想到你,想到孩子们,想到这个家。
海尔茂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?
娜 拉 不,千万别写信。
海尔茂 可是我总得给你寄点儿——
娜 拉 什么都不用寄。
海尔茂 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得帮点儿忙。
娜 拉 不必,我不接受陌生人的帮助。
海尔茂 娜拉,难道我永远只是个陌生人?
娜 拉 ( 拿起手提包)托伐,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。
海尔茂 什么叫奇迹中的奇迹?
娜 拉 那就是说,咱们俩都得改变到——喔,托伐,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。
海尔茂 可是我信。你说下去!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——?
娜 拉 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。再见。(她从门厅走出去)
海尔茂 ( 倒在靠门的一张椅子里,双手蒙着脸)娜拉!娜拉!
(四面望望,站起身来)屋子空了。她走了。(心里闪出一个新希望)啊!奇迹中的奇迹——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。
——剧终
1879 年《玩偶之家》的首演,曾经给欧洲社会带来如同暴风雨一般猛烈的震撼,因为这部剧作尖锐地提出了家庭中妇女地位的问题,给当时欧洲保守而又伪善的社会道德一记响亮的耳光,由此它也成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经典。
课文节选的第三幕是全剧的高潮,同时也是结局部分。阅读时,注意抓住人物言行前后的变化,分析娜拉和海尔茂这两个人物的性格,理解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本质,从而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。
《玩偶之家》属于“社会问题剧”,这是易卜生创造的戏剧类型,强调在舞台上呈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(而不是古代王公贵族或骑士游侠的传奇故事),在戏剧中直接讨论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。阅读时,要注意结合作品体会这些特点,还要注意分析作品中的“戏剧性事件”以及“突转”手法的运用,领略剧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。
This is a companion discussion topic for the original entry at 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pkuschool/xbz000/%e7%ac%ac%e5%9b%9b%e5%8d%95%e5%85%83/12-%e7%8e%a9%e5%81%b6%e4%b9%8b%e5%ae%b6%e8%8a%82%e9%80%89-%e6%98%93%e5%8d%9c%e7%94%9f
-
北欧的一种风土舞曲,轻快清爽 ↩︎
Last edited by @suen 2024-08-18T02:33:34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