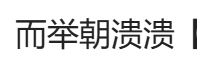论屈原
六国之并于泰也,秦智而六国愚,而其愚之甚者,莫如楚。其君愚,其臣愚,其举国皆愚。
有一不愚者,且群起而嫉之。呜呼!欲其国之不亡也,得乎!
楚地半天下,带甲百万,自成、穆以来,常雄于天下。一旦而顿,为泰弱,何哉?夫国之所
以振兴者,曰有人而已。楚入战国来,其君既庸下,其臣亦皆碌碌无可纪者。张仪之愚怀王,如
戏婴儿,如狙公之弄狙,而举朝溃溃【 1 】。独一原者,知其诈,愤其奸,痛哭垂涕而告之,而终不
悟。不惟不悟,且群以为狂,以为诽谤,必不使其身容于朝廷之上。吁!亦可哀也已。
迨贾生作赋吊之,谓原以其才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如此伤之至矣。然亦未知其心焉。
夫屈子其可去乎哉?其忍去乎哉?身为宗臣,准诸箕、干之义,有死而已,有囚而已,行吟泽畔,
憔悴枯搞,则亦微子【 2 】遁荒之意耳。而倦倦宗国,冀其君之一听,则心良苦矣。宁子[ 3 】邦无道
则愚,屈子其可谓愚者矣!然正惟屈子之不愚,所以成其愚也。正惟其君之愚,臣之愚,举国之
愚,而屈子尤不能已于愚也。竭屈子之愚,而君可以不愚,臣可以不愚,举国可以不愚,而楚可
称雄于天下。独奈何愚者之群,不谅其愚也。且其言曰:举世皆醉而我独醒,举世皆浊而我独清。
夫浊者,愚之本也。醉者,愚之状也。当其时,秦以术愚人,而六国者皆在醉死梦生中也,巠些
如是,屈子又安适也哉?
伊尹之任,伯夷之清,柳下之和,疑皆倚于一偏,得孔子孟子取而论之,而天下皆知其为圣。
使屈子生孔孟之前,得至人以表其微,俾天下后世知臣子之于君国,有如是。其缠绵诽侧,不容自己者,则三纲得以益明,五常得以益显。夫圣与愚相反者也,而屈子则庶几以愚而造于圣。
呜呼!不谅于屈子之愚而愚屈子之愚者,独楚/~之愚乎哉! 賞析本文,從觀點到論述到文筆。
下面是一篇对所引文字的整体赏析,分为「观点」「论述」「文笔」三个层面进行分析,供参考。
一、观点
- “愚”与“智”的冲突:
文章开篇指出“六国之愚,尤以楚为最”,并强调“其君愚,其臣愚,其举国皆愚”。在此“愚”的氛围中,偏有一个不愚者——屈原,却遭到众人的排斥和嫉妒。作者用极端的对比手法,凸显了屈原的“孤独”与“悲壮”。这种“孤独”不仅仅是性格、情感上的落差,更表现为价值观与政治智慧上的格格不入。
- 屈原的忠愚:
虽然文中多次提到“愚”,但作者并非真的认为屈原愚钝,而是强调屈原以“愚者之姿”体现其忠贞,反衬出他的高尚。所谓“正惟屈子之不愚,所以成其愚也”,说明屈原的“愚”其实是“兼具先见之明与坚贞操守”的“愚忠”。他选择死守理想、死守楚国,不愿背弃“君国”的大义,这是作者眼中最动人的地方。
- 对国家兴亡的核心看法:
作者认为,一个国家要想振兴,“曰有人而已”。换言之,真正的智者与忠臣对于国家生死存亡意义重大。而楚国的覆灭正是因为君臣上下均昏庸,或不听劝、或不知情。若“竭屈子之愚”,便能使楚国重振雄风,可惜他们“愚者之群,不谅其愚”,终致楚国衰亡。
- 历史上的映照与呼应:
文末提到了尹伊、伯夷、柳下惠等先贤,也提到了孔孟对于这些人物的阐发。作者用“假若屈原生在孔孟之前,得至人表彰”的假设,突显出屈原的历史地位本应与伯夷、伊尹这类“圣人”相映照,只是时运不济、遭逢昏主,以至于被误解。
二、论述
- 层层对比,突出人物形象:
• 对比一:秦与六国
作者认为“秦智而六国愚”,并从中特别突出了楚国最为“愚笨”,先给读者设立一个强烈的反差。
• 对比二:举国皆愚,唯屈原不愚
屈原站在一个极端位置,他的“清醒”在一群“昏醉”者面前显得尤为突兀,也注定悲剧。
• 对比三:愚而称雄vs.愚而自亡
楚曾“带甲百万,自成、穆以来,常雄于天下”,却因为上下昏庸而迅速衰亡。“不愚”的屈原本可挽救楚国,但终究被当作“诽谤”和“狂人”而被排斥。
- 层次推进,严密精巧:
文章从“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”六国与秦的比较切入,继而聚焦到楚国,再点名屈原。接着举例:张仪游说、群臣溃溃,而独屈原看破诡计却不为所用。然后作者自然过渡到屈原的忠贞与无奈,在最后更将屈原与历史上的古之贤者(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、孔孟)连贯起来,结尾得出“愚乃是屈原成圣的途径”的耐人寻味的论断。这种从外到内、从面到点、从现实到历史再到价值判断的布局,使文章论述环环相扣。
- 设问与感叹的巧妙使用:
文中多次用“呜呼!”“吁!”“何哉?”“夫……”等文字标志,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。设问如“欲其国之不亡也,得乎?”、“何哉?”等,都推动读者思考:楚国既有这么好的地理与军事条件,为何落得亡国结局?屈原又为何宁死不去他国?这一系列疑问与感叹,塑造出激昂、悲凉并存的论述氛围。
三、文笔
- 批判峻烈,慷慨悲凉:
• 文章指出“其君愚,其臣愚,其举国皆愚”,语气之决绝,毫不留情面,带有强烈的讽喻色彩。
• 针对屈原受到群体误解的描写,如“且群起而嫉之”“以为诽谤”,更凸显作者对于楚国群氓不识贤才、楚王昏庸的强烈批判。
• 文中的一连串感叹句和“呜呼”“吁”等古典叹词,营造出激越的悲愤氛围,与屈原人生悲剧的主题交相呼应。
- 善于用典,历史纵横:
作者引述或暗示了多个典故和人物:
• “张仪愚怀王”点出战国纵横家如何利用君王之愚。
• “伊尹之任,伯夷之清,柳下之和”暗示历史上不同类型的贤臣或高士,都有各自闪光点,最终被孔孟阐发,从而列入“圣”范畴。
• “微子遁荒”映射屈原出走汨罗江、流放途中的“犹盼转机而终不得”的苦情。
这些用典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,也使得文字更具古雅之美。
- 语言流转,情理交融:
全文语言以议论为主,夹带叙述、抒情成分。可以看到:
• “愚”字反复出现,却涵义不同:既指楚王与群臣的“愚”,也指屈原对理想坚守的“愚”(实际是一种“智慧”)。这种矛盾而对立的词义反复出现,产生回环咏叹的韵味。
• 文章既有强烈的理性批判,如分晰政治局势、权谋得失,又有饱满的情感色彩,如对屈原遭遇的哀叹、“亦可哀也已”等。融理性与情感于一炉,让语言更富感染力。
小结
综合来看,本文以评述战国纷争、楚国积弱为背景,聚焦屈原被误解、被排挤的悲剧命运。作者从“愚”与“智”这个核心概念出发,揭示“昏庸的国君与顽固的大众如何对待一个清醒者”,最终让屈原成为“愚者”眼中的“愚人”,但在实质上,他却是最忠诚且最通达的大智者。整篇文章观点鲜明、层层铺陈,文笔激昂深沉,富有抨击时政与讽刺的力量,同时也寄寓了对忠臣贤士不被理解的哀痛与悲愤。这种历史纵横、激烈慷慨、悲凉哀婉的笔触,正是一种典型的古文雄浑之风,也使得对屈原的评价更加令人回味不已。
从全文看,作者为什么在文未发出“独楚人之愚乎哉"的溉叹?
要理解作者为何在文末发出“独楚人之愚乎哉?”的慨叹,需要结合全文思路与论点加以综合分析。
一、全文的核心思路
- 对屈原及楚国的批判与同情:
文中作者先批评“楚君愚、臣愚、举国皆愚”,而唯有屈原“独不愚”,却被视为“狂”“诽谤”,被群起排斥。作者对此深感慨叹与惋惜。
- “愚”与“智”的多重含义:
• 楚王群臣之“愚”,指的是真正的昏聩不明、随波逐流。
• 屈原之“愚”,则是一种表面看来“固执己见”,实际上却是坚守忠贞、保持远大智慧的不屈精神。
- 屈原的悲剧与楚国的兴亡:
作者以“有人而已”四字说明“国之所兴,在有人”,屈原本可辅佐楚国,但他的“智”却被群体的“愚”压制,因此整篇文章的立意不仅在于揭示屈原的悲剧,也在反思人群的盲从、国家的误判。
二、为何文末发出“独楚人之愚乎哉?”的慨叹
- 对楚国上下的愚昧进行“升华”式批判:
文章前大段篇幅都在谈“楚国君臣愚不可及”,“张仪之愚怀王,如戏婴儿”,以及“独有屈原不愚却被众人排挤”。到了结尾,“独楚人之愚乎哉?”是一种反问,带有“难道只有楚人如此愚昧吗?”的意味。借此升华文章主旨:并非只有楚人会犯这样的大错,而是当今世上若有类似情形,也同样会让贤能之士蒙难。
- 呼应“不谅于屈子之愚而愚屈子之愚者”
在文末作者说:“不谅于屈子之愚而愚屈子之愚者,独楚人之愚乎哉!”意思是:那些不理解屈原的“愚忠”,反而嘲笑他的人,难道只有楚国人么?作者借这一设问,指向更普遍的人性弱点——对真正坚守正义或真理的人,人们往往会不理解甚至排斥。
- 感叹中带有普遍意义的警示:
“独楚人之愚乎哉?”并不只是在责怪历史上的楚国人,更是一种讽喻,警示后世:每个时代都有可能重蹈“群愚”排斥“独醒者”的覆辙。作者一方面深痛楚人的昏庸使屈原被陷害,一方面也要告诫当时或后世:若再现类似局面,则屈原式的悲剧仍会发生。
- 突显结尾的感叹与讽喻力度:
从修辞上看,这句反问句让文章在结尾时戛然而止,余味无穷。它既保留了前文对楚国亡国原因的聚焦,也将批判矛头向更多可能存在的“愚众”蔓延,带着讽刺意味和警世效果。
小结
作者在文末发出“独楚人之愚乎哉?”的慨叹,既是对全文前面所批判的“楚国上下之愚”做一收束,也是透过屈原的悲剧反问“难道只有楚人这样吗?”。这层反问拔高了文章主旨,表明:不仅是楚人,当世乃至后世若也像楚国君臣那样盲从昏昧,就难免重演“群起而嫉之”的悲剧。由此,作者在一声沉重的自问中引人深思,令读者对历史与现实产生更深刻的警醒。
Last edited by @suen 2025-01-14T10:57:57Z